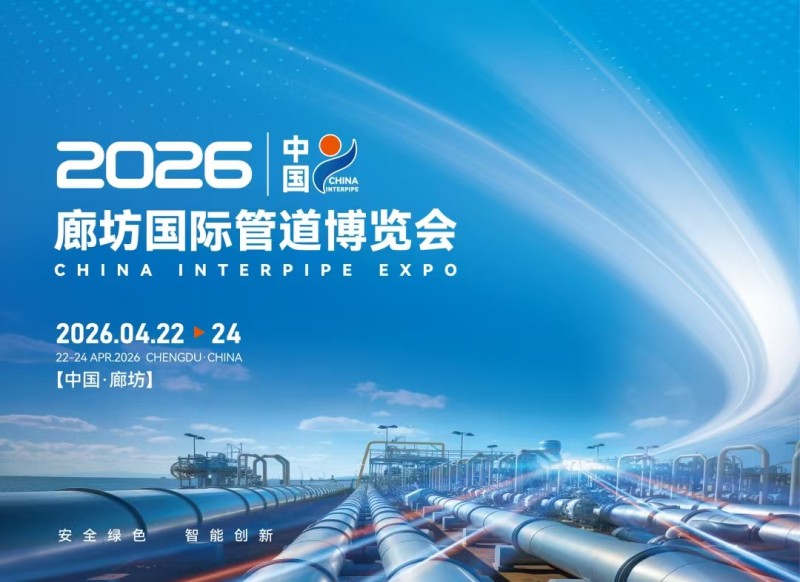接(1):玉瑶最开心的就是青梧也偷偷爬上来陪他的日子,他们总有说不完的话,玉瑶还喜欢青梧偷偷带给她的书。“国父说过,中国有四万万人,一半是男人,一半是女人,女子从前的地位很低,所以要主张民权主义,要让女子和男子享有相同的地位。”每当这时,玉瑶的眼神比天上的星子都亮。“真好,青梧,中华民国真好。你说,父亲届时会允许我考女校吗?”而每到这时,青梧总是沉默不语,他忧伤的眼神穿过沉沉的夜色,无处安放。
“玉瑶,这个秋天少爷就要去武昌读师范了。”少年的声音里有羡慕也有一丝怅惘。“嗯,我知道啊,哥哥告诉我了,真替他高兴,哥哥还说现在生逢乱世,军阀混战,只有教育才能兴国。”少女清澈的眼神充满了向往。“青梧,那你呢?”女孩忽然想起什么一般,咬了下唇,“我?我也不知道,我爹让我回来帮他,现在咱们沙洋地界的纱厂就属盛家盛福绸庄生意最好,老爷信任我爹。”
“那,你愿意吗?”少女紧紧地盯着少年的眼睛。“我,我想继续读书。”少年低下头去。“青梧……”少女突然伸手扶住少年的手臂,“哥哥从未曾将你当做奴仆,我亦如是。且父亲早已放了你的奴籍,你读书不比哥哥差,不必委屈求全。”女孩默了默,放开手臂,“男儿当自强,你懂吗?”女孩不再说话,重新躺下仰望星空。“虽然我是女孩,但我一定会努力成为国父口中自强独立的女子,你信我。”
“玉瑶,我当然信你,我也会努力的。”少年乌黑的瞳孔里盛满少女的笑脸,撑着手臂,看向星空,“我会努力成长为能站在你身边的人……”少年在这个夏夜郑重地在心里许下第一个愿望。星光下女孩脸上似乎覆盖着一层细细柔柔的沙,又似乎蒙着一层轻轻淡淡的纱,还像铺子里最华丽的缎子,流光溢彩。
红衰翠减梧桐老,瑟瑟秋风起。
金桂飘香的季节里,我没看到那个少爷鲜衣怒马赴金陵的意气,却听到了书房老爷的咆哮。“承启,你看看这世道,南京已经没了,鬼子已经在安庆了,你还不走,你是要我们盛家断子绝孙吗?”紧接着屋子里传来“咚”的一声,“父亲,老爷!”少年和另一个苍老的声音同时响起。“少爷,您就听老爷的话吧!再不走就来不及了,城里的火车站现在已经乱套了,伤兵源源不断,车根本开不出去,满地都是人。”一道焦急的声音里满是祈求。
“庄管家,你去,将准备的物件再检查一遍,这事,由不得他。”另一道疲惫的声音里我仿佛能看到老爷儒雅随和的脸上的哀伤。我轻轻地摇摆着叶子,心里不安极了,最近哪怕在睡梦中我好像都能听到远方天空传来隆隆炮火声,有时甚至能看到火烧云一般的云霞,极致绚烂又美丽。可我知道,那不是云霞,这片屋顶这几个月来几乎成了两个少年和少女的根据地,他们经常说的一些词,“战争,日本鬼子,民众,灾难……”我不太懂,但我读得懂他们眼中的哀伤和提起日本鬼子的愤怒。如同那天落在我旁边两只鸽子眼中的哀伤,它们说它们的家人都被炮弹炸死了,它们说要飞去远方,可远方是哪里呢,哪里的天空下还有净土。
一阵极淡的玉兰花香气袭来,我转动身子,“青瑶,嘘!”少女穿着时下女学生最流行的白色斜襟小袄,下身一条淡绿色的裤子,满头的青丝早已剪去,留了齐耳短发,婴儿肥的小脸满是严肃。“啪”的一声,我惊讶地瞅着,我脚下的一片青瓦被掀了起来,少女跪着趴了下去。
“父亲,鬼子的铁蹄已经踏上我们的家园,偌大个中国哪里还能放下一张安静的书桌。”屋子里少年跪在地上,头埋在双臂中,哭泣的声音从他的喉咙深处传来,似无声的呼喊,浸透了秋的悲凉。女孩捂着嘴跪立起来,泪水顺着指缝滴落,渗入我的根里,好苦。我努力地探着身子,坐在椅子上的男人佝偻着脊背,挪开目光看向窗外,眉头紧紧地蹙着,仿佛一夜之间将沧桑刻在了脸上。
“孩子,保家卫国那是军人的事情,你还是个孩子啊!咱盛家传到这一辈就剩下你和玉瑶,你要有个好歹,咱盛家就万劫不复,而我盛继业就是天大的罪人。”男人撑着扶手站了起来,浑身哆嗦,“你若执意要弃笔从戎,那就当没我这个父亲,我归天之日亦不需你来摔盆。”书房门哐的一声推开又哐的一声关上,男人踉跄着离开,我被窜起的风吹得歪到一边,屋顶的女孩呆呆地坐着,屋内的少年笔直地跪着。秋风打着旋刮尽了院落中间掉落的黄叶,一片肃杀。
两个少年穿着一水的藏蓝色中山装,戴着同色的宽边帽子,提着竹纹的皮箱青竹一般立在二门垂花门处。天井中的菊花开得正好,硕大的花朵黄金般地明媚耀眼,香气四溢。
“走吧,走吧,老爷是不会见你们的。”穿着长袍的男人终于从抄手游廊处晃晃悠悠转了出来,叹息着将水烟袋别在腰上,“爹。”青梧跪了下来,“庄叔。”承启也跪了下来。“孩子起来,都起来。”梳着圆圆发髻的中年女子身着一件洗得泛白的蓝花旗袍,蹲下身子用力地托着两个少年的手臂,额角的碎发在八月的阳光下竟闪过一抹银色。“不,兰姨,庄叔,且受我一拜,我定会视青梧为手足,相互扶持的。”肤色白皙的少年挣开女人的手臂深深地拜了下去。“少爷,你别这么说,你说过国家兴亡,匹夫有责,这是我自愿的。”肤色略黑的少年拽起旁边的身子。
“孩子,都起来吧。我不懂那么多大道理,但我知道,谁抢了我们的土地,哪怕拼了命,咱们也要夺回来。”男人长长吁了口气,笑得无比凄楚,“我和老爷在这老宅等你们回来,你们方便时就捎封信回来,出门在外,千万机灵点。”说完,再不回头,挥挥手转身去了。女人抓起地上的搭链挂在儿子身上,嘴唇哆嗦着,挤出一丝笑来,抓过儿子和承启的手紧紧握在一起,“有炒的油茶,有南瓜粑粑,有熏的肉肠,有……”女人哽咽着说不出话来。
“哥哥,青梧哥。”少女身着明亮的水蓝色旗袍,上面绣着精美的缠枝花蔓,乌黑的短发,一侧别在耳后,露出精巧白皙的耳垂,缓步走了过来。“青梧哥,你一定要平安回来,我会一直等你,你和哥哥是我的英雄。”女孩在月色下朝他挤出一个羞涩的笑容。时间仿佛被定格一般,青梧只听到自己擂鼓般的心跳,逆光下的女孩像一株盛开的兰花一般,将这世上所有的繁华与美好种在了青梧的心里,在这一刻扎了根。
1938年8月,大宅子里少了两个英气勃勃的少年郎,遥远的广州黄埔军校多了两个相濡以沫的战友。
二进门堂屋的门直到月色铺满整个中庭方才吱“吱拉”一声打开,一个男人步履蹒跚地走到院子的亭子中坐下。执起酒壶斟满,却不忙喝,男人扭头叹息: “老庄,出来吧,咱老哥俩喝一杯。”老庄,出来吧。咱老哥俩喝一杯。”悉悉索索的声音里,抄手游廊阴影里晃出一道身影。“花间一壶酒,独酌无相亲。从此以后,你我二人兄弟相称。”一身长衫的男人双手举起一杯酒,向着蹒跚而来的身影深深地拜了下去。